今日热点回放教你五分钟把花呗的钱提现出来转到银行卡里面(必看)
|
无论语言的起源和诞生如何模糊不清——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有一点确定无疑,人类使用语言,是为了更好地交流、表达和创造。 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索绪尔认为语言的一大特征在于“约定俗成”,也就是“符号”和“意义”之间的联系并非唯一,而是带有某种任意性。这是古典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在古典的谱系中,对语言的泛滥化、工具化有着高度的警觉,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辩若讷”;佛教的基本原则有“八正道”,其中之一是“正语”,即远离一切虚妄不实之语言;马太福音的告诫则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不过遗憾的是,人类从来没有按照智者们的要求来使用语言,语言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几乎是以一种现实货币的状态出现:膨胀,溢出,曲解,拜物。在语言的使用中,人类固然展示了其理智、洞见和创造的一面,但也有很多时候沦于盲目、愚蠢和谵妄。这种谵妄症至现代而达高峰。 其一是将语言视作意识形态的载体,并将其彻底工具化为一种“洗脑术”。纳粹德国在这一点上堪称“表率”,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克莱普勒用词汇表的形式深入分析了纳粹是如何偷换概念和重塑意义,将“语言”改造为一种贫瘠、夸张、假大空的口号和标语。比如英雄,它“原本是一个促进人类事业的行动的实施者”,但是第三帝国的宣传语言却将其滥用于所有参与残忍侵略战争的人,并为此颁发众多的奖章,对此克莱普勒痛心疾首地批判说:“当英雄主义越是沉静,越少面对公众,越少有装饰性的时候,才越是纯洁,越具有意义。……对于正义的、真实的英雄主义,纳粹主义从来就没有公开地提及过。由此,它篡改了整个概念,并毁坏了其名声。” 出于对这一语言控制术的抵抗,后结构主义者们强调语言自身的革命,并以游戏的方式来解构一切确定的价值和意义。不过可见的历史事实是,后结构主义者的这种“革命”并无显著的政治实效,它倒是在大众文化的层面收获了层出不穷的“跳蚤”:广告语、辩论赛、传销方案、深夜电台、综艺节目以及脱口秀…… |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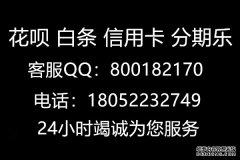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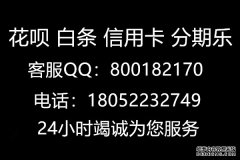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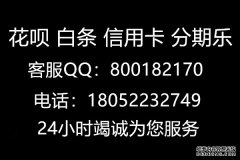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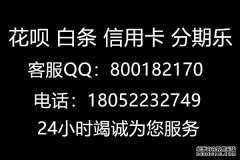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