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山里 31岁的特教校长与97个不普通的孩子
|
从黔西南州府兴义市出发,到达普安县特殊教育学校,要绕过太多大山,地图上的路线轨迹永远是弯弯曲曲的。这所贵州唯一建在乡村的九年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目前有97名在校寄宿生,“他们都不是普通的孩子。”31岁的黄国荣,在这里当校长已经五年了,他用整整五年,为当地脑瘫、智力障碍、情绪与行为障碍、自闭症等特殊孩子建起了第二个家。 “特殊教育不是一个很容易获得成就感的职业。”特殊孩子们的记忆时间是很短的,学过的东西转瞬即忘,在黄国荣看来,这个职业是在与时间对抗,需要用长时间的“重复”,去巩固孩子们的短时记忆,用最耐心的培育和等待,去期盼孩子们能够掌握一些最基础的生活技能,那些进步,就像无尽长夜中瞬间绽放的花火,“但你知道的,只要有那么一瞬,我们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午休时间,黄国荣(左二)和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特殊孩子的第二个家 每天上午九点一刻到九点四十五这段时间,是普安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大课间。下课铃一响,学生们会在老师的带领下涌入操场。学校操场面积不大,学生们都就位了,也只填满操场面积的三分之一。如果只看背影,这些学生似乎与同龄正常孩子没什么不同,偶尔有孩子好奇地向陌生人看过去,一样会露出一个顽皮的笑脸。
普安县特殊教育学校,是贵州唯一建在乡村的特教学校。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特殊孩子”与普通孩子的差异,出现在课间操音乐响起的那一刻。队列中动作最整齐划一的永远只有站在第一排的老师,他们身后,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基本跟上音乐的节拍,而低年级的孩子,多是跟随音乐,晃动着身体。这套操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师生们面对面完成一套手舞并跟随音乐唱歌,大多数学生仅能凭借律动挥舞手臂,他们偶尔会被歌声带动,突然发出些简单的声调。 31岁的黄国荣是这所特殊学校的校长,他个头不算太高,长着一张苗族传统的宽圆脸,走在学生队伍中,像是个孩子王。“大课间也是孩子们在户外进行康复训练的机会,孩子们要借此学会跑、跳、行走以及大声说话。”黄国荣说,康复训练的过程长久且缓慢,比如像这套课间操,能做到这个程度,学校的老师们几乎用了一个季度的时间。
孩子们在做手舞并跟随音乐唱歌。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超30万人口的县市都应设立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普安县人口在35万上下,唯一的这所特殊教育学校建立在县域南部,也是贵州唯一一所建在乡村的特殊教育学校。 这所2016年正式开学的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根据入学年份和孩子的不同程度,进行分班分年级教学,学生的年龄在7岁-15岁不等。我国将与正常儿童在各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的特殊儿童分为8类,黄国荣任校长的这所特殊教育学校,是普安县脑瘫、智力障碍、情绪与行为障碍、自闭症等特殊孩子的第二个家。 成为最年轻校长 今年31岁的黄国荣已经在这所学校里当了五年的校长。无论是五年前,还是当下,在整个贵州的特教学校中,再没有哪个校长比黄国荣更年轻。
大课间时,黄国荣(中)和老师学生一起唱跳手舞操。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他2014年毕业于贵州毕节学院(现称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是这所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的第一届本科生。这是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在全国3005所高等学校中,开设特殊教育专业的只有不到2%的高校。 报考特殊教育专业,是黄国荣自己的选择,这与儿时的经历有关。爷爷的弟媳一般被叫做叔婆,在黄国荣的故乡,叔婆也被叫作“幺奶”,“她是听觉语言障碍人士,但她从小很照顾我,会带我一起去山上放牛,砍柴,割猪草。”在黄国荣的记忆里,幺奶质朴,勤劳,有时看到自己在山上因为贪玩受伤,幺奶会近乎本能地心疼和着急。小时候的黄国荣不懂如何与她沟通,只知她对自己好,心里感激,又同情幺奶的命运。 黄国荣的家乡在普安县的另一头,北部的龙吟镇被称作中国苗族第一镇,在这里少数民族聚居,97%的人都是苗族。小时候,寨子里没有人听说过所谓的“特殊教育”,整个普安县也没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当时年纪小,就觉得学这个专业有用嘛,能帮助很多人,能让像幺奶一样的特殊人群有个出路。” 很少有家里人了解黄国荣自己的选择,更没有多少人看好这个专业。在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亲戚们道喜的电话都是兴冲冲地打来,垂头丧气地挂掉。“特殊教育专业是干什么的?”舅舅听说后也跟着叹气,“平时让你教表弟做功课都很困难没耐心,你怎么选这个专业,这不就意味着要去教那些不正常的人?” 多年以后,黄国荣也会承认自己低估了特殊教育的难度。“原来只以为特殊教育就是教他们语文、数学知识,真正上了大学,和真实的学生有了接触,才明白其中的难度比想象的大得多。” 以重复抵御重复 在成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之前,黄国荣曾经被借调到普通小学当过老师。两所学校中孩子们的差异有多大?黄国荣说,以最简单的数字教学为例,在普通小学这只是一个课时的内容,但在特殊教育学校,要想教会孩子们对于数字的认知,老师们至少要付出一个星期甚至更多的时间。 上午的大课间结束后,二年级的学生要上语文课。这学期开学不久,坐在教室第二排的然然的书已经很旧了,书页处早被卷出了一些毛边,上课不过五分钟,这本书已经被他翻来覆去翻了两遍。坐在然然身后的小隆同样是自闭症患儿,每隔十几二十秒抬起小臂擦拭嘴角是他的习惯动作,与然然不同,他的刻板行为带有自伤性,日积月累下来两侧嘴角边的脸颊总是红肿发黑。
开学不久,然然的书已经被翻得很旧了。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在这节课上,为了让孩子们准确描述一张图画上的内容,任课教师大概用了一刻钟的时间,其中的多数时候,老师在重复提问、重复提及图片中物体的名称,除此之外,老师还要努力维持这个仅有十二三名学生的课堂纪律。与普通学校不同,这所学校的教室里除了孩子们的课桌,也有老师们办公的格子间。每一个课堂上,除了有任课老师,在教室另一角落办公的老师随时准备成为课堂的助教。“坐好,看老师这里”,这是老师们在课堂上最常说的话。 重复地去教学,重复地输出同一个知识点,重复地去讲同一句话,是特殊教育老师们的主要的工作。特别是当面对自闭症患儿的刻板行为时,教学就更要重复了。
为了方便照看学生,老师们的办公室、格子间也在教室里。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有特教老师开玩笑说,教育一个特殊儿童所消耗的精力几乎与教好十名普通学生一样,这说法听起来会认为有些夸张。而事实是,据教育部2016年统计数据,全国特殊教育师生比为1∶2至5.5(其中,聋校1∶2至5.5、盲校1∶2至4、启智校1∶2至3.5),而九年义务制内的普通学校,师生比则基本维持在1∶18左右。从另一个角度说,对单一个体而言,特殊教育工作者面对学生所要付出的精力确实更多。 以时间抗衡时间 相对于单一的自闭症,包括自闭症在内的智力障碍,在学校中更为普遍。在普安县特殊教育学校,99%的儿童都存在智力障碍。黄国荣说,智力障碍孩子生理、行为、认知、情感、意志、语言、性格等各方面都有自己独有的特殊特点。例如记忆方面,一个行为或者一个知识大概只需要20或者30分钟的时间就会被孩子们遗忘。有的孩子在学校待的时间长了,“爸爸妈妈”也被遗失在了脑海里,“他们的记忆力很短,有的可能只记得10天内对自己最好的人。” 曾经网络中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的是“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但是现实是,科学证明鱼的记忆根本没有这么短暂,而特殊儿童的记忆力,有时却不及鱼长。 在这个角度下,“重复”也是被老师们认为可能击败“短时记忆”的唯一法宝。比如课间操的一个动作,对于一种颜色的认识,甚至是对于一项生活的常识或者自理技能掌握,黄国荣说,这些都要经过特教老师日复一日,变着花样儿的引导和告知,时间付出的多了,才有可能迸发出一些令人惊喜的火花。 黄国荣讲起在2017年,有家长为了听孩子叫一声妈妈而将孩子送来学校,“她说孩子养了10年,从来没有听儿子鹏鹏喊过妈。”黄国荣唯一的方法,就是“重复”,将鹏鹏平常能够接触到的物品上贴满母亲的照片,把能够被他听到的音乐改为与“妈妈”相关的旋律,甚至连自己手机铃声,也成了“妈妈”二字的口播呼喊。“这些对他来说似乎一直无效,孩子看起来也并不理解。”直到3个月后,鹏鹏的母亲去接他。黄国荣当时其实已经泄了气,“我就跟他说,‘你妈妈来了,快叫妈。’结果没想到,他真的就转过头喊了一声沙哑的‘妈’。”孩子的母亲一愣,下一秒就有眼泪涌出眼眶。她突然跪在地上,没抱住孩子,抱住了黄国荣。 黄国荣讲到这里,双手也摆出一个拥抱的姿势,“那时候我刚毕业一两年,实话讲有一瞬间觉得很不好意思,但被这样的情绪拥抱着,又觉得很感动”。 坦白地说,老师们“重复”的更多意义,有时并不在于记忆,而在于培养一种生存的惯性。这种惯性对于普通孩子来说,是近乎于本能的常识,几乎可以不被引导和教育。但对于特殊儿童,这些就成为了孩子们接受特殊教育的全部目的。很久以后,黄国荣说,或许特殊教育的成功与幸福就来自这里吧,让一个不会叫妈妈的孩子开口叫妈妈,让不会写字的孩子握笔写字,让生活无法自理的孩子,掌握生活的常识和技能。 一草一木也有功劳 可在特殊教育学校里,“障碍”也分程度。一部分特殊儿童的患病源头在于基因,他们会因为父母双方家族基因的问题,而患有多重障碍。 这是最棘手的状况。“你知道吗,这些病多少有点欺负人的。”黄国荣说,有的患儿会集合脑瘫、癫痫、多动症、智力障碍、情绪障碍多重问题,“一般是三到五种,多重障碍的孩子康复训练的难度非常大,而且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孩子寿命普遍不高,人生在半路就夭折了。” 黄国荣很少与人讲这些让人觉得遗憾的事,更多时候,如所有特教老师一样,他说的最多的,是孩子们刚送进来时候的样子——因为与现如今学校里的孩子们相比,前后表现确实差距巨大。 有的孩子从前没有自理能力,曾在教室里随地大小便,现在已经会了上厕所。有的自闭症患儿从前每天都重复着一条固定行走路线,也从不与人交流,到后来他会主动叫老师的名字。一些孩子们能画漂亮的画,能唱动听的歌,跟着老师学会表演,还在全省与普通中小学同台的评比中拿了奖。黄国荣猜想,普通学校即便培育出走进清北的学生,老师们的成就感也未必比得上特教老师这一刻的万千欣喜。 特教老师们都爱讲如“鹏鹏”一样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总能让人看到希望。而事实也是,当人们走进这所特教学校,愿意开始了解这些孩子,他们就会向人们展现那些生涩的、又渴望被关注到的热情。这些特殊的孩子有的也会求抱抱,看到人们拿出手机,也想搂着你一起拍照。
黄国荣和学校的孩子。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尽管普通孩子的认知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是绝大多数特殊儿童难以达到的,“可只要你愿意和他们耐心沟通,你就会懂得他们的意思。就像最开始,我们老师会被一些有情绪障碍的孩子‘打’,但事实上,这只是因为他们想与老师打个招呼而已。” 在黄国荣看来,在特殊教育学校,除了老师,任何寻常之物都有可能是老师手里的教具,甚至一草一木也都有功劳。寻常在大门口起到观赏意义的水池鱼塘,能让学生们感知和认识真实的鱼类;一路相迎的彩色轮胎也并非只起到装饰作用,它们让孩子们更容易地认识了色彩;就连小径中的石子路也承担着功能性,“有的学生脚是跛的,我们会寄希望于晴天的时候,孩子们能够踏上石子路,这样通过石子矫正和按摩,也能起到一定的康复作用。” 校长、桥梁与演技大师 学校里能够流利表达的孩子并不多。口舌操就成为了学校康复训练的一部分,“跑火车”和“舔白糖”是黄国荣使用最多频率的办法。“‘跑火车’嘛,就是先使嘴唇松弛下来,再吹动嘴唇。”说着他开始做起示范,先是轻轻努嘴,气流传唇而过,就发出了“嘟嘟嘟”的声响。“比赛舔白糖是给孩子们设计的引导游戏,也是为了让孩子们的舌头不再僵硬。”说着,黄国荣也会将舌头探出口腔作示意。 黄国荣讲话时,说着说着,只要说出一个可以用动作表达的句子,就会用行动来进行示范。当他觉得语言的表达简单空洞时,肢体语言就会迅速补位,旁边的倾听者也转变成了观众。这几乎可以称作是特教经历带来的一种职业习惯,他经常会将自己想象成一名演员,“普通的小孩子,你要想和他交流,就得蹲下身子,去达到一个和他视线平等的高度。特殊的小朋友更需要这种平视,不光是身体上,有时也在于心理上。你想和他交流,就得扮演得像他一样,去成为他的玩伴。”
在五年级的班级里,老师正在辅导学生进行单位换算。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每一位特教老师都想成为一座桥梁。“原来我们遇到过一个小孩,他写的每一个数字都与咱们普通的阿拉伯数字相反,比如6会被写成9。所以我想,其实他们看到的世界就是和我们不一样。”两个世界总需要一个介质去连接,才能创造交流可能。黄国荣说,对于很多欠发达地区的特殊儿童来说,特教老师是极少有机会走进孩子们世界的人,他们也是连接孩子们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桥梁。 教育行业中的小圈子 虽然老师们给孩子讲解时示范行动很正常,“但是当这种模仿的状态成为了日常习惯,有时候你会觉得学校外的人看你总是怪怪的”。无可否认的是,相对于看到孩子们取得进步时的欣喜,压抑的情绪在特教老师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特殊教育老师其实是很难能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在这种状态下,老师们也要消化来自外界的不理解和偏见。” 在省内,不同的特殊教育学校也会互相拜访交流,在普安县隔壁,盘州特殊教育学校校长严云元也到过黄国荣的学校。到了中午,大家一起在饭桌上吃饭,交流的内容总离不开学校里的事,聊天除了聊学生,也聊各自的压力和郁结。 盘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地理位置上临近普通小学,闲暇时特教老师会到学校操场上打球,偶尔也有普校老师从旁经过。“有一次听到老师们窃窃私语,在惊讶原来特殊学校的老师也会开口讲话。” 从未走进过特殊教育群体的人,很难理解特教老师们的工作。老师们不否认特殊教育在整个教育行业中有小圈子,但实质更像是老师们一起抱团取暖。黄国荣说,自己有一次去杭州出差,萍水相逢的一位老师也是特教人,两人就坐在路边聊了两个多小时,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严云元觉得,能为老师打破这种压抑的,很多都来自孩子们的进步。“我们这一行的工作是很平淡的,不容易找到成就感。日积月累下来,当你看到来的时候不会走路的脑瘫患儿,开始能走路了;曾经用手抓饭吃的孩子,已经用勺子吃得很好了;从前不理人的孩子,开始愿意跟你打招呼了,就会得到特别大的慰藉。”这一刻的到来,对于特教老师而言像是漫长黑夜中的一束烟花,它似乎能燃尽循环往复的无望和疲倦,照亮整个长夜。 “我们的学生”和一个愿望 当特教老师们坐在一起,用来区分不同类型学生的词汇只有两个,“普通学生”和“我们的学生”。 在老师们看来,“我们的学生”也有普通孩子鲜能超越的特质。“他们比普通孩子踏实,他们的思路和反应回馈都是非常直接单纯的,他们甚至不会偷懒,执着的心性远超普通学生,当你让他们专心去完成一件事的时候,孩子们几乎从不让你失望。”黄国荣说,现在因为学校才办了5年,各种教学内容还在补充,为了孩子能更好的融入社会,初步针对大龄在校生开展职业化的技能培训。 距离学校不到一百米处,一家小型汽修店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写有“普安特校汽车美容教学基地”的字样。这是黄国荣不久前与老板谈下的合作,已经有零星的年纪稍长、障碍程度稍轻的孩子来这里实习培训,“老板说孩子们在洗车的时候,他们洗得比老板洗得都干净。”黄国荣听了很开心。 黄国荣总说,特殊教育,是立足于孩子们最后的出路来考虑当下教育的。这个出路有多重要?重要到,无论这些特殊孩子在学校中康复到了多好的程度,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如果没有真正的出路,他们就仍然不能自食其力。“你要知道,他们的命运与学校、家庭以及孩子本身有着密切关系的。三者应该保持密切的教育协作关系,一旦有一方失手,那么令人遗憾的故事,就难免要发生。”
孩子们在教室上课。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四月初的时候,马云乡村校长计划公布了2020年的校长入选名单,黄国荣的名字出现在了20位校长当中。知道自己入选获奖之后,黄国荣低头想了想,说获奖与否并不重要,但他是特别开心的,“因为这就意味着特殊教育还是得到了一些关注,更多人也会了解特殊教育是怎么一回事。特教老师们教育的成功、孩子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学习成果,也有可能得到更全面的宣传”。 对“我们的学生”,黄国荣和老师们倾注了太多关注与情感,也由此期待有所“回报”,或者说,是总有一个心愿希望实现,那就是最终“离开学校会生活”,“这是我和同事们最想看到的事情,也是我们一直努力去实现的愿望。”黄国荣说。 (文中提及的学生名字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陈荻雁 |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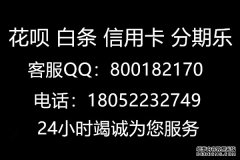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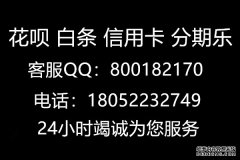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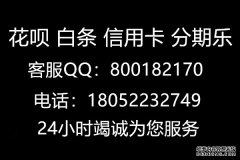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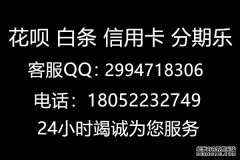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