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导演张杨回归剧场:这次回来是学习|专访
|
张杨在排练《探长来访》现场。朱朝晖 摄 《探长来访》是二十世纪中叶最经典的英语戏剧之一,不仅曾多次改编为影视作品,从1946年起,话剧《探长来访》在英国伦敦西区连演10年,和连演57年的《捕鼠器》、连演20年的《黑衣女人》一起,被誉为“去伦敦西区必看的三大名剧”。此次,“鼓楼西”特邀新京报对话《探长来访》导演张杨,揭秘创作背后的故事。话剧《探长来访》将上演至5月9日。 与孟京辉同期探索先锋戏剧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是中央戏剧学院87级导演系学生的张杨便与导演系88级研究生的孟京辉开启了先锋戏剧的实践与探索之路,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便是在孟京辉所编的《先锋戏剧档案》记录了一次谈话,描述了1989年发生在中央戏剧学院的一次事件:孟京辉和张杨与校方争论是否排练并演出《等待戈多》。 这一事件由孟京辉和张杨发起,当年中央戏剧学院里,包括施润玖,刁亦男, 蔡军, 廖一梅,张有待,韩青,柳青,王世同等胸怀大志的有志青年,决定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天,即1989年12月31日,在戏剧学院操场边的巨大煤堆上演出萨缪尔·贝克特著名的荒诞剧《等待戈多》。此举被校方所闻,予以制止。此次谈话录音系孟京辉和张杨在被校方找去谈话后,对是否进行演出进行的讨论。当时全程录音,由孟京辉珍藏,后整理成文。 随后张杨也曾在1990年元旦,孟京辉导演的第一部戏剧,改编自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名剧《升降机》中,扮演过“蒙面拍照人”。大学期间,张杨与张一白、刁亦男、蔡尚君、孟京辉等始终一起尝试先锋戏剧的排演,在彼此的作品里相互客串。尤其在1992年,张杨排演毕业大戏,改编自阿根廷小说家曼努埃尔·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中,该剧由刁亦男编剧,并邀请了当年已经毕业,张杨的好友贾宏声担任了该剧的主演之一。
张杨。朱朝晖 摄 【对话】 新京报:你导演的两部戏都是改编自国外的作品,为何对此比较钟爱? 张杨:其实并不是。就我个人而言,如果可能的话,当然还是希望原创的作品最好。但就戏剧而言,创排原创剧本非常难。 除非长期从事戏剧创作,拥有一定的基础与感觉,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找到了很多方式方法,才可以去做原创。对于我这样,已经那么长时间没有从事戏剧工作的人来说,可能相对成熟的剧本创作起来会简单一点。 新京报:这么多年排演话剧,与过去相比会有一些全新的感受吗? 张杨:相比起拍电影,排话剧当然还是很舒服的。导演可以完全静下心来和演员们进行创作,每天亲眼看着他们一点一点的改变,这个挺有意思的。不像拍电影,每天的事情特别多,导演要做各种各样很多的决定,也在做像制片人一样的工作,其实劲儿都没用在创作上。排话剧,我的所有时间,基本上都用在跟演员的沟通与日常排练里,从这个角度讲,很幸福。 新京报:会产生某种压力吗? 张杨:排一个戏,中间总会有一个阶段会遇到焦虑的时刻,很正常。尤其是第一次完整的把戏联排出来之后,导演想的更多的还是在最终舞台呈现上,是否有更多提高的可能性。这种焦虑,不光是导演(有),演员也会有,但往往过了这段焦虑期,大家都会找到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
《探长来访》定妆照。朱朝晖 摄 新京报: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接受邀请,回归戏剧? 张杨:并非是刻意的选择,排戏这事我已经想了很多年了。毕竟我当年在中戏就是导演系,毕业时排过一个戏之后,一晃也30年了。前两年去参加乌镇戏剧节,孟京辉跟我说,找时间一定要回来排戏,其实心里边一直有这个打算。 这两年鼓楼西的制作人李羊朵,我们一直没有断联系。她也一直在给我推荐“鼓楼西”有版权部分的剧本,当我看到《探长来访》,便决定先从这部作品入手。 新京报:众多推荐,为什么选择了《探长来访》? 张杨:戏剧其实还是在于文本本身,很多经典的戏剧,虽然从头至尾有大量的台词,但通过这些文本,你还是会发掘很多具有吸引力的东西。另外,《探长来访》吸引我的还是作品的现实性,跟我们今天的时代背景、针对的问题都很接近,这是今天我们排这部戏的意义所在。虽然写的是1910年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是人面对现实的困境,跟今天差不多,相信观众也能从中找到某种参照。 新京报:你如何解读《探长来访》? 张杨:这部作品最主要讲的还是某些人性的罪恶问题。人通常都很容易遗忘,包括对于很多历史问题。而戏剧的意义就是提示每个人很多东西不能遗忘,必须要去面对曾经,要学会去忏悔。 实际上,《探长来访》的反转就在于,最终“探长”通过以步步紧逼的调查方法,把剧中五个人物内心的“肮脏”通通呈现出来了,证明这一家每个人都要对女工的死负责。最终讨论的还是人性的善恶标准如何确定与社会道德取向等非常现实的问题。
《探长来访》排练照。朱朝晖 摄 新京报:与电影相比,合作《探长来访》的演员你会有自己的内心标准吗? 张杨:这部作品里,李梅与杜功海其实都是我上学时候的师弟师妹,不管在影视或戏剧都是非常好的演员。其他演员也都是通过招募试戏,通过选拔出来的鼓楼西签约演员,因此从表演功底到对于戏剧的理解完全不是问题。可能从我的角度,关注的还是演员在表演过程中表现的自然流畅,“不要有戏剧范,不要拿舞台腔”,至于其他的戏剧理念,我们都很一致。 新京报:如今你的“戏剧观”会跟三十年前有所不同吗? 张杨:其实我跟演员们开始也聊到,这次回来算一个学习的过程。电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事,不管是看过的片子,读过的书,方方面面更多都是跟电影有关。这些年可能也在看一些戏剧,但相比专业戏剧人来说,那就不值一提。有时候你看的不够,看的少可能就会限制你戏剧创作方面的想象力与方法,包括我们所说的戏剧观的更新,至少目前我自己还处在上学时建立的那么一套戏剧体系。 当年上学的时候,除跟孟京辉做了很多先锋戏剧,大家的思路和想法都是往先锋的方向去走,对我的帮助很大。因此这次回归,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先用一个戏开始做一些尝试,未来可能再继续深入。 新京报:当年排毕业戏《蜘蛛女之吻》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张杨:那时候一切都比较简单,基本上没任何的资金支持,都是同学、朋友来帮忙。毕业戏选择《蜘蛛女之吻》是因为这部小说本身很独特。整部作品没有任何的旁述,从头至尾就像正常人的对话一样。所以当年刁亦男用小说改编了这部戏,而贾宏声与李洪涛分别演的是剧中“牢房”里的两个人。 相比于现在,那时候我们的表现形式非常简单,但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比较新颖了,包括时空的运用、语言的表达,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那时候学生真的没有钱排戏,现在回想有点“贫困戏剧”的感觉。那一次的排戏体验给我的个人感觉是特别好的,当年的观众也非常喜欢这部戏,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把它重排,现在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排成。 新京报:你提到这部作品的这些人,如今在自己的领域都有了自己的成绩,对你而言,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吗? 张杨:跟现在完全是两种概念,那个时候其实都是大家绑在一起做事,因为那时候还是学生,其实后来孟京辉在“先锋戏剧档案”里边,对于那一代人有着很详细的记载。蔡尚君、张一白、刁亦男、廖一梅,甚至包括张楚那时候做音乐,做美术的柳青等等很多人。在那个时代的中央戏剧学院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创作氛围,后来就再没有了,这一批人真的是影响了中国电影(600977,股吧)和戏剧的发展。 新京报记者 刘臻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卢茜 |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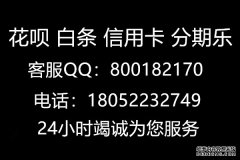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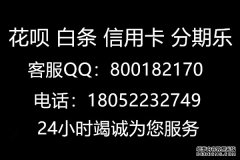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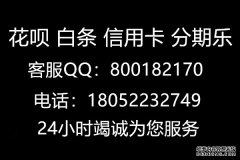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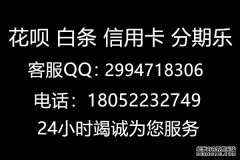




评论列表